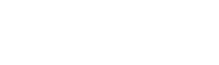赌博下注平均(3)
最近,有关中国公司和信义义务的争论仍然硝烟弥漫。哈佛大学法学院弗雷德(JesseM. Fried)教授即将发表一篇重要论文,指责某中国互联网巨头通过“在开曼注册,在美国上市”的手法,规避美国法中关于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的严格规定,因为美国法院对其控制股东无管辖权,而开曼的公司法却没有规定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缺陷,将美国投资者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同时,弗雷德教授也将矛头指向了在中国发行的中国存托凭证(CDR)。他认为“中国内地的公司法没有明确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因此中国投资者通过投资CDR可以成为美国公司实质上的控制股东,却可以不履行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进而侵犯美国的中小投资者。”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信义义务。
信义义务是考察一国商法是否优良的试金石。目前,对中国法律的怀疑乃至对中国战略甚至中国文化的怀疑,正在成为美国一种流行的看法,特朗普对华政策也受此影响。
其实,中国也不缺少信义传统,“仁义礼智信”中就有信义的元素。在民国时,中国信托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翻开1931年程联先生编著的《世界信托考证》一书,皇皇一千余页,扉页上印着“信而有托”四个大毛笔字,可以感到中国人不缺少对信义义务的领悟力。
信义义务的原则在我国,特别是基金行业没有充分和深入地实践,与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必然联系,主要病因在于人的观念和制度。西方数百年的观念和制度探索历程,在中国需要浓缩在几十年内实现,我们这一代人任务艰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今后要加强基金业特别是私募基金的受托人的信义义务,需要从以下几个路径着力下手:
第一,现在许多业内人士甚至监管者和法官对于信托关系和信义义务缺乏认识。
对信义义务的相关研究、宣传和培训必须到位,要让有关人士认识到信义义务的几个重要的法律特质。这里,笔者归纳如下:
信义义务效力的法定性:不可以合同法思维替代信托法思维
在认定信义义务时,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仅看合同条款,而忽视了信义义务的丰富含义,信义义务是超越合同文本的法定义务,不限于合同的具体约定,它有极高的要求。
在2018年爆发的私募基金风险事件中,部分专家仅仅以合同约定的义务清单来认定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认为如果私募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失联,不宜将接管责任超出合同范围延伸到托管机构。这是典型的以合同法思维代替信托法思维的做法,显然是将信义义务仅仅视为合同义务了,忽视了其法定性。
这种观点强调托管银行应当而且必须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好相关职责,但是决不能超越合同赋予的托管义务,否则容易将外部风险传导到银行体系。银行是金融体系稳定的“压舱石”,如果损害了银行体系稳定性,将会动摇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背后隐藏着一种不合理的政策化思维而非法治化思维,更不是信义法思维,意在保护银行安全,而非投资者利益。
这种偏颇的思维在日本也同样存在。日本著名的信托法专家东京大学法学院樋口范雄教授在《信托与信托法》一书中写道:“日本的司法裁判经常受到‘信托也是合同’的观点的不良影响。既然是合同,在了解双方当事人具体协商事项时很看重双方合意。不过,信托的本质是‘信任基础上的委托’,所以,除当事人合意外,焦点要看受托人如何才算尽到了善良注意义务。”
信义义务适用的广泛性:基金业的各种法律结构均适用信义关系
信义义务除适用于信托关系外,还适用于公司法中的董监高和公司的关系,适用于合伙企业中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私募基金普遍采用的有限合伙企业中的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之间的关系。可见,即使资管业的法律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并不全是信托结构,但是,均适用信义关系,因为资管业的法律组织形式无非三种:信托、公司和合伙,均在信义关系的涵盖中。如果说“让资管业回归大信托格局”尚有可商榷之处,但说“让资管业回归信义关系”则无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