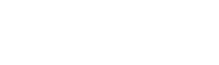LV娱乐真人游戏
1 919年,岁次己未。这一年对于68岁的林纾来说颇不平静。去年春天,北大那批青年教师办的刊物上,一个叫“王敬轩”的读者来信推崇“林先生”是“译笔健雅”的“当代文豪”,居然被杂志编者反斥一顿,说“林先生”翻译的都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的“闲书”。毫不奇怪,两年前他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后,就被“新青年”盯上了,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都陆续对之进行讥刺嘲讽。更早的恩怨,也许是钱基博所分析的那样,为桐城人物被“章门之徒”逐出北大而不平;还有一笔账,即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里排出的“十八妖魔”,包含了桐城家法里的列代祖师。
今年2、3月里,林纾给学生张厚载替他在《新申报》张罗的专栏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又刊出两封公开信,《致蔡鹤卿书》(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再答蔡鹤卿书》(1919年3月25日《大公报》,次日又在《新申报》刊出)。小说引起的波动比公开信更大,《妖梦》咒骂“鬼中三杰”,影射的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从长相上进行挖苦和羞辱,实在显得很低级;更为人不齿的是《荆生》里动用武力来解决争端,被敏感的新文化人物认定这似乎是要召唤军阀来镇压他们。于是,林纾被确认为无能的反对者,大家忘记他在公开信里说了什么话还值得思考了。各家报刊媒体纷纷转载的就是这两篇小说,有时还加上了特别的按语,比如“想用强权压倒公理”云云,今天的话说来,就是故意要“晒”林纾。而到了4月,陈衍主编的《文艺丛报》第一期上,还刊出林琴南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的文章,学理思想如何,也就都不那么受人重视了。《新申报》的主笔张厚载被北京大学开除了,林纾为他送行,赠《序》里说“张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若无所戚戚于其中者”。

1922年的林纾,时年71岁,刊《人间世》第14期(1934.10.20)
平心而论,林纾本来并不反对白话文学,他在世纪之初就为杭州《白话日报》撰写《白话道情》了;1919年3、4月他还在《公言报》连续发表他的《劝世白话新乐府》和《劝孝白话道情》。至于提倡新文学,引入外国文学,他翻译的《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等,这些后生谁没读过?诚然,白话文学需要更“进化”的形态,外国文学需要更高明的译才;可是处在新旧过渡的时代,难道求新就需要以“损旧”为必然代价吗,一蹴而就的新真会很新吗?《公言报》上发表的《腐解》,提到自己的“七十之年,去死已近”,林纾此前从未觉得自己是守旧派,但在后辈更为激进态度的对照下,他感觉自己好像难免也被迫坠入腐朽的老顽固队伍中了。他生气地在《新申报》那个文言笔记小说的专栏里写道:
吾年七十,而此辈不过三十,年岁悬殊。我即老悖颠狂,亦不至偏衷狭量至此。……我老廉颇顽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惧也。来!来!来!
由此看来,文言小说里的那种近乎谩骂的方式,在老迈却易怒的林纾这里,顶多算是不注意修养和分寸的一种失态表现;老年人认死理,觉得后辈晚生不懂事,发脾气下来,大概就是这样吧——后来“新青年”们变老了,也未尝不曾有类似的表现。这年林纾和唐文治议论废经、与族侄林怿论师道的文章,实则也都是在宣泄他对新文化运动激进姿态的不满。《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里说过“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这样无可奈何的话;然而,“新青年”们没有放过他,从此之后毁谤之言不绝于耳。甚至连这一年他第五个女儿出生,后来都被鲁迅捉弄了一番,称“曾在一个药房的仿单上见过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谢丸药的功效”(《论照相之类》)云云;事实上林纾甚至根本没有小老婆。

林纾的山水画
在已经经营了二十年的文学翻译“作坊”里,至少从产量上看,这种衰老退化的感受还并不明显。1919年,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们又译出了十来种外国小说,五花八门的,很出风头。这一年,北京上海的市民读者打开《小说月报》第十卷,会发现每一期开篇依然都是他们熟悉的林琴南:起初有从西方歌剧情节编译的《泰西古剧》,之后又加进来一部西方中世纪故事集《妄言妄听》。还出现过一部中短篇的哈葛德《豪士述猎》,讲述的还是英国人在黑非洲的冒险经历。这种风光的气势已经维持不了太久了,下一年的《小说月报》目录里会出现一个新栏目“小说新潮”,主持人是沈雁冰;此人很快会切断手里这个杂志与“林纾公司”的固定关系,并即将不再刊发“林译小说”。沈雁冰对林纾的反感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后者所被塑造的形象,他对“林译小说”本身也许并不太了解。很多年后,已经成为著名小说家茅盾的沈雁冰撰写了一部《汉译西洋文学名著》,选目中排在荷马史诗之后的中古文学作品《屋卡珊与尼各莱特》,就是《妄言妄听》里的《阿卡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