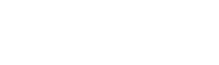周作人:“日常ö
与鲁迅不同,周作人在后人中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呈现出一种复杂面相,而且至今如此。年轻时,周作人也曾紧随社会潮流,倡导新文化,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也在那个特定环境下产生了巨大反响。此外,他还注重译介外国新思想,成为那一时期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他也和鲁迅等人共同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坚持去女师大上课,以示支援。但他与左翼文学运动一直有些隔阂,因此显得不够革命。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应是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即明显表现在其散文的平和、冲淡之气质,也就是表现在其文字中的“日常性”。周作人贴近日常,写故乡的野菜、写苦茶、写点心,在日常中发现生活的丰富与超然,用“不带一丝火气”的声调叙述人生,并用此种态度完成自己的一生。这也是我们了解周作人为人为文的重要向度。今天是周作人的忌日,经出版社授权,我们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董炳月的《周作人的“日常”》一文,来了解周作人的“日常”,也借此文纪念他。
(导语:张进)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
周作人的“日常”
撰文 | 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周作人1967年5月6日离开人世,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他在八十岁那年的日记中表明心迹,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但他这理想未能实现。他留下了大量著作与译作,留下了许多照片。他“活”在文学史上,“活”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
周作人的神情,可谓超然、冷静。他中年之后的每一张照片,几乎都在展示那种出家人式的超然、冷静。周作人认为自己是和尚转世,在《五十自寿诗》中称“前世出家今在家”。光头,形象上也接近出家人。相由心生,文如其人。周作人的超然、冷静,是可以用其作品来印证的。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那些说古道今、回忆往事的散文,谈茶、谈酒、谈点心、谈野菜、谈风雨的散文。本质上,周作人的超然与冷静,与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关。这种日常性,亦可称为“世俗性”或“庶民性”。在周作人这里,“日常性”是一种价值,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书写方式。因此他追求“生活的艺术”,主张“平民文学”,获得了“自己的园地”。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也曾是忧国忧民、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五四时期,他投身新文化建设,倡导新村运动,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周作人获得超然、冷静的日常性,是在中年之后,确切地说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他在1923年7月18日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人生观开始改变。1925年元旦写短文《元旦试笔》,声称“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思想起伏颇大。1926年经历了“三一八惨案”的冲击,1928、1929年间写《闭户读书论》《哑巴礼赞》《麻醉礼赞》等,于是进入“苦雨斋”,喝“苦茶”并且“苦住”,最终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日常”的价值观。不幸的是,1939年元旦遭受枪击,在内外交困之中出任伪职。所幸,日本战败,晚年周作人在社会的边缘回到了日常性。《老虎桥杂诗》中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回归。
上文所引“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一语中的“人间”是个日语汉字词,意思是“人”。鲁迅的《人之历史》一文,1907年12月在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时,题目本是《人间之历史》。1926年鲁迅将其编入《坟》的时候,改文题中的“人间”为“人”。精通日语者,中文写作难免打上日语印记。不过,周作人这里使用的“人间”一词,大概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人的“人间情怀”。他1926年6月7日写的杂文《文人之娼妓观》,就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那句“我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之前”,并说“这样伟大的精神总是值得佩服的”。词汇的微妙体现了思想的微妙。